|
| |
小学数学论文:数学思维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发布时间:2019-04-08 20:1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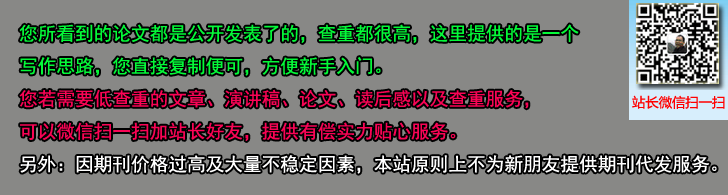
小学数学论文:数学思维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帮助学生学会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是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所设定的一个基本目标。以国际上的相关研究为背景,对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突出数学思维进行具体分析表明,即使是十分初等的数学内容也同样体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数学思维形式及其特征性质。
关键词:数学思维;小学数学教学
对于数学思维的突出强调是国际范围内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如由美国的学校数学课程与评估的标准和我国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关于数学教育目标的论述中就可清楚地看出。然而,就小学数学教育的现实而言,上述的理念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下的认识:小学数学的教学内容过于简单,因而不可能很好地体现数学思维的特点。以下将依据国际上的相关研究对这一观点作出具体分析,希望能促进这一方向上的深入研究,从而能够对于实际教学活动发挥积极的导向作用。
一、数学化:数学思维的基本形式
众所周知,强调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正是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数学课程的内容一定要充分考虑数学发展进程中人类的活动轨迹,贴近学生熟悉的现实生活,不断沟通生活中的数学与教科书上数学的联系,使生活和数学融为一体。”[1]就努力改变传统数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病而言,这一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从更为深入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在此则又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应当如何去处理“日常数学”与“学校数学”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即使就最为初等的数学内容而言,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数学的抽象特点,而这就已包括了由“日常数学”向“学校数学”的重要过渡。
例如,在几何题材的教学中,无论是教师或学生都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研究对象并非教师手中的那个木制三角尺,也不是在黑板上或纸上所画的那个具体的三角形,而是更为一般的三角形的概念,这事实上就已包括了由现实原型向相应的“数学模式”的过渡。再例如,正整数加减法显然具有多种不同的现实原型,如加法所对应的既可能是两个量的聚合,也可能是同一个量的增加性变化,同样地,减法所对应的既可能是两个量的比较,也可能是同一个量的减少性变化;然而,在相应的数学表达式中所说的现实意义、包括不同现实原型之间的区别(例如,这究竟表现了“二元的静态关系”还是“一元的动态变化”)则完全被忽视了:它们所对应的都是同一类型的表达式,如4+5=9、7-3=4等,而这事实上就包括了由特殊到一般的重要过渡。
应当强调的是,以上所说的可说是一种“数学化”的过程,后者集中地体现了数学的本质特点:数学可被定义为“模式的科学”,也就是说,在数学中我们并非是就各个特殊的现实情景从事研究的,而是由附属于具体事物或现象的模型过渡到了更为普遍的“模式”。
也正由于数学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抽象的模式而非特殊的现实情景,这就为相应的“纯数学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例如,就以上所提及的加减法运算而言,由于其中涉及三个不同的量(两个加数与它们的和,或被减数、减数与它们的差),因此,从纯数学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何依据其中的任意两个量去求取第三个量。例如,就“量的比较”而言,除去两个已知数的直接比较以外,我们显然也可提出:“两个数的差是3,其中较小的数是4,问另一个数是几?”或者“两个数的差是3,其中较大的数是4,问另一个数是几?”我们在此事实上已由“具有明显现实意义的量化模式”过渡到了“可能的量化模式”。
综上可见,即使就正整数的加减法此类十分初等的题材而言,就已十分清楚地体现了数学思维的一些重要特点,特别是体现了在现实意义与纯数学研究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当然,从理论的角度看,我们在此又应考虑这样的问题,即应当如何去认识所说的纯数学研究的意义。特别是,我们是否应当明确肯定由“日常数学”过渡到“学校数学”的必要性,或是应当唯一地坚持立足于现实生活。
由于后一问题的全面分析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在此仅指明这样一点:与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对于学生很好地把握相应的数量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这正是国际上的相关研究、特别是近年来所兴起的“民俗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尽管“日常数学”具有密切联系实际的优点,但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例如,如果仅仅依靠“自发的数学能力”,人们往往就不善于从反面去思考问题,与此相对照,通过学校中的学习,上述的情况就会有很大改变,这就是说,纯数学的研究“在帮助学生学会使用逆运算来解决问题方面有着明显的效果”;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局限于特定的现实情景,所学到的数学知识在“可迁移性”方面也会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一般地说,学校中的数学学习就是对学生经由日常生活所形成的数学知识进行巩固、适当重组、扩展和组织化的过程,这就意味着由孤立的数学事实过渡到了系统的知识结构,以及对于人类文化的必要继承。这正如著名数学教育家斯根普所指出的:“儿童来到学校虽然还未接受正式教导,但所具备的数学知识却比预料的多……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是从(学校教学)活动中组织和巩固他们的非正规知识,同时需扩展他们这种知识,使其与我们社会文化部分中的高度紧密的知识体系相结合。”[2]
当然,我们还应明确肯定数学知识向现实生活“复归”的重要性。这正如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所指出的:“数学的力量源于它的普遍性。人们可以用同样的数去对各种不同的集合进行计数,也可以用同样的数去对各种不同的量进行度量。……尽管运算(等)所涉及的方面十分丰富,但又始终是同一个运算──这即是借助于算法所表明的事实。作为计算者人们容易忘记其所涉及的数以及他所面对的文字题中的算术问题的来源。但是,为了真正理解这种存在于多样性之中的简单性,在计算的同时我们又必须能够由算法的简单性回到多样化的现实。”[3]
总的来说,这就应当被看成“数学化”这一思维方式的完整表述,即其不仅直接涉及如何由现实原型抽象出相应的数学概念或问题,而且也包括了对于数量关系的纯数学研究,以及由数学知识向现实生活的“复归”。另外,相对于具体知识内容的学习而言,我们应当更加注意如何帮助学生很好地去掌握“数学化”的思想,我们应当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情境设置”与“纯数学研究”的意义。这正如弗赖登塔尔所指出的:“数学化……是一条保证实现数学整体结构的广阔途径……情境和模型,问题与求解这些活动作为必不可少的局部手段是重要的,但它们都应该服从于总的方法。”[4]
二、凝聚:算术思维的基本形式
由以下关于算术思维基本形式的分析可以看出,思维的分析相对于具体知识内容的教学而言并非某种外加的成分,而是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具体地说,这正是现代关于数学思维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即指明了所谓的“凝聚”,也即由“过程”向“对象”的转化构成了算术以及代数思维的基本形式,这也就是说,在数学特别是算术和代数中有不少概念在最初是作为一个过程得到引进的,但最终却又转化成了一个对象──对此我们不仅可以具体地研究它们的性质,也可以此为直接对象去施行进一步的运算。
例如,加减法在最初都是作为一种过程得到引进的,即代表了这样的“输入—输出”过程:由两个加数(被减数与减数)我们就可求得相应的和(差);然而,随着学习的深入,这些运算又逐渐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们已不再仅仅被看成一个过程,而且也被认为是一个特定的数学对象,我们可具体地去指明它们所具有的各种性质,如交换律、结合律等,从而,就其心理表征而言,就已经历了一个“凝聚”的过程,即由一个包含多个步骤的运作过程凝聚成了单一的数学对象。再如,有很多教师认为,分数应当定义为“两个整数相除的值”而不是“两个整数的比”,这事实上也可被看成包括了由过程向对象的转变,这就是说,就分数的掌握而言我们不应停留于整数的除法这样一种运算,而应将其直接看成一种数,我们可以此为对象去实施加减乘除等运算。
对于所说的“凝聚”可进一步分析如下:
(一)“凝聚”事实上可被看成“自反性抽象”的典型例子,而后者则又可以说集中地体现了数学的高度抽象性,即“是把已发现结构中抽象出来的东西射或反射到一个新的层面上,并对此进行重新建构”。[5]这正如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皮亚杰所指出的:“全部数学都可以按照结构的建构来考虑,而这种建构始终是完全开放的……当数学实体从一个水平转移到另一个水平时,它们的功能会不断地改变;对这类‘实体’进行的运演,反过来,又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这个过程在一直重复下去,直到我们达到了一种结构为止,这种结构或者正在形成‘更强’的结构,或者在由‘更强的’结构来予以结构化。”[6]例如,由加法到乘法以及由乘法到乘方的发展显然也可被看成更高水平上的不断“建构”。
(二)以色列著名数学教育家斯法德(A.Sfard)指出,“凝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阶段:1.内化;2.压缩;3.客体化。其中,“内化”和“压缩”可视为必要的准备。前者是指用思维去把握原先的视觉性程序,后者则是指将相应的过程压缩成更小的单元,从而就可从整体上对所说的过程作出描述或进行反思──我们在此不仅不需要实际地去实施相关的运作,还可从更高的抽象水平对整个过程的性质作出分析;另外,相对于前两个阶段而言,“客体化”则代表了质的变化,即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看一件熟悉的事物:原先的过程现在变成了一个静止的对象。容易看出,上述的分析对于我们改进教学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所说的“内化”就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点:我们既应积极提倡学生的动手实践,但又不应停留于“实际操作”,而应十分重视“活动的内化”,因为,不然的话,就不可能形成任何真正的数学思维。另外,在不少学者看来,以上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熟能生巧”这一传统做法的合理性。
(三)由“过程”向“对象”的过渡不应被看成一种单向的运动;恰恰相反,这两者应被看成同一概念心理表征的不同侧面,我们应善于依据不同的情景与需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必要的转换,包括由“过程”转向“对象”,以及由“对象”重新回到“过程”。
例如,在求解代数方程时,我们显然应将相应的表达式,如(x+3)2=1,看成单一的对象,而非具体的计算过程,不然的话,就会出现(x+3)2=1=x2+6x+9=1=…这样的错误;然而,一旦求得了方程的解,如x=-2和-4,作为一种检验,我们又必须将其代入原来的表达式进行检验,而这时所采取的则就是一种“过程”的观点。
正因为在“过程”和“对象”之间存在所说的相互依赖、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因此,一些学者提出,我们应把相应的数学概念看成一种“过程—对象对偶体”procept,这是由“过程”(process)和(作为对象的)“概念”(concept)这两个词组合而成的。,即应当认为其同时具有“过程”与“对象”这样两个方面的性质。再者,我们又应很好地去把握相应的思维过程(可称为“过程—对象性思维”〔proceptual thinking〕)的以下特征:(1)“对偶性”,是指在“过程”与相应的“对象”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2)“含糊性”,这集中地体现于相应的符号表达式:它既可以代表所说的运作过程,也可以代表经由凝聚所生成的特定数学对象;(3)灵活性,是指我们应根据情境的需要自由地将符号看成过程或概念。数学中常常会用几种不同的符号去表征同一个对象,从而,在这样的意义上,上述的“灵活性”就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意义:这不仅是指“过程”与“对象”之间的转化,而且也是指不同的“过程—对象对偶体”之间的转化。例如,5不仅是3与2的和,也是1与4的和、7与2的差、1与5的积,等等。
综上可见,在算术的教学中我们应自觉地应用和体现“凝聚”这样一种思维方式。
三、互补与整合:数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
以上关于“过程—对象性思维”的论述显然已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互补与整合这一思维形式对于数学的特殊重要性。以下再以有理数的学习为例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首先,我们应注意同一概念的不同解释间的互补与整合。
具体地说,与加减法一样,有理数的概念也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如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商,算子或函数,度量,等等;但是,正如人们所已普遍认识到了的,就有理数的理解而言,关键恰又在于不应停留于某种特定的解释,更不能将各种解释看成互不相关、彼此独立的;而应对有理数的各种解释(或者说,相应的心理建构)很好地加以整合,也即应当将所有这些解释都看成同一概念的不同侧面,并能根据情况与需要在这些解释之间灵活地作出必要的转换。
例如,在教学中人们往往唯一地强调应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这一角度去理解有理数,特别是,分数常常被想象成“圆的一个部分”。然而,实践表明,局限于这一心理图像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学习困难、甚至是严重的概念错误。例如,如果局限于上述的解释,就很难对以下算法的合理性作出解释:
(5/7)÷(3/4)=(5/7)×(4/3)=…
其次,我们应注意不同表述形式之间的相互补充与相互作用。
这也正是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突出强调学生的动手实践、主动探索与合作交流:“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与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教师应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向学生提供充分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7](2)由于实践活动(包括感性经验)构成了数学认识活动的重要基础,合作交流显然应被看成学习活动社会性质的直接体现和必然要求,因此,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上述的主张就是完全合理的;然而,需要强调的是,除去对于各种学习方式与表述形式的直接肯定以外,我们应更加重视在不同学习方式或表述形式之间所存在的重要联系与必要互补。这正如美国学者莱许(R.Lesh)等所指出的:“实物操作只是数学概念发展的一个方面,其他的表述方式──如图像,书面语言、符号语言、现实情景等──同样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次,我们应清楚地看到解题方法的多样性及其互补关系。
众所周知,大力提倡解题策略的多样化也是新一轮数学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学生生活背景和思考角度不同,所使用的方法必然是多样的,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想法,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提倡计算方法的多样化。”[7](53)当然,在大力提倡解题策略多样化的同时,我们还应明确肯定思维优化的必要性,这就是说,我们不应停留于对于不同方法在数量上的片面追求,而应通过多种方法的比较帮助学生学会鉴别什么是较好的方法,包括如何依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地去应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显然,后者事实上也就从另一个角度更为清楚地表明了“互补与整合”确应被看成数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
最后,我们应清楚地看到在形式和直觉之间所存在的重要的互补关系。特别是,就由“日常数学”向“学校数学”的过渡而言,不应被看成对于学生原先所已发展起来的朴素直觉的彻底否定;毋宁说,在此所需要的就是如何通过学校的数学学习使之“精致化”,以及随着认识的深化不断发展起新的数学直觉。在笔者看来,我们应当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课程标准中有关“数感”的论述,这就是,课程内容的学习应当努力“发展学生的数感”,而后者又并非仅仅是指各种相关的能力,如计算能力等,还包含“直觉”的含义,即对于客观事物和现象数量方面的某种敏感性,包括能对数的相对大小作出迅速、直接的判断,以及能够根据需要作出迅速的估算。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应明确地肯定帮助学生牢固地掌握相应的数学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需要的时候能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数量方面作出准确的刻画和计算,并能对运算的合理性作出适当的说明──显然,后者事实上已超出了“直觉”的范围,即主要代表了一种自觉的努力。
值得指出的是,除去“形式”和“直觉”以外,著名数学教育家费施拜因曾突出地强调了“算法”的掌握对于数学的特殊重要性。事实上,即使就初等数学而言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出“算法化”的意义。这正如吴文俊先生所指出的:“四则难题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奇招怪招。但是你跑不远、走不远,更不能腾飞……可是你要一引进代数方法,这些东西就都变成了不必要的、平平淡淡的。你就可以做了,而且每个人都可以做,用不着天才人物想出许多招来才能做,而且他可以腾飞,非但可以跑得很远而且可以腾飞。”[8]这正是数学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即一种重要算法的形成往往就标志着数学的重要进步。也正因为此,费施拜因将形式、直觉与算法统称为“数学的三个基本成分”,并专门撰文对这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了分析。显然,就我们目前的论题而言,这也就更为清楚地表明了“互补与整合”确应被看成数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
综上可见,即使是小学数学的教学内容也同样体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数学思维形式及其特征性质,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应作出切实的努力以很好地落实“帮助学生学会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这一重要目标。
(2008年11月获省教科院一等奖)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2.
[2]小学数学教育──智性学习[M].香港:香港公开进修学院出版社,1995.74.
[3]Didactical Phenomenology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s[M].Reidel.1983.116—7.
[4]作为教育任务的数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124.
[5]E Beth,J Piaget.Mathematical Epistemology and Psychology[M].Reidal.1966.282.
[6]发生认识论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9.
[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数学教育现代化问题[A].21世纪中国数学教育展望[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9—20.
|
| |
|
|